
《仁術、中(zhōng)和與天道——中(zhōng)華文(wén)化身體(tǐ)學(xué)與生命倫理(lǐ)思想的多(duō)元曆史建構》,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
馬家忠,南京中(zhōng)醫(yī)藥大學(xué)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研究中(zhōng)心研究員。
臨在于嘈雜與潦草(cǎo)的學(xué)術時風,細讀馬家忠君的這部書稿,凝思一下關于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和中(zhōng)華生命倫理(lǐ)學(xué)的這些事,百念膠結,難以自已。
我想說的是:首先,中(zhōng)華民(mín)族本應有(yǒu)自己獨行鶴立的生命倫理(lǐ)元素,并應該是人類道德(dé)文(wén)化的一個重要部分(fēn),但因為(wèi)曆史上沙障與蠻遠(yuǎn)戈壁的阻隔,幾乎沒有(yǒu)易學(xué)文(wén)化和生命倫理(lǐ)思想的交流或互生;我們的醫(yī)學(xué)的封閉僅僅是對于自由意志(zhì)的争取而缺乏世界主義的氣勢,我們如同科(kē)學(xué)技(jì )術一樣,閉關自守的結局,使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和由其養育的身體(tǐ)人文(wén)難以克服其非科(kē)學(xué)化内在品行;醫(yī)學(xué)僅僅是維系或應付人們的健康與疾病救治的需求,作(zuò)為(wèi)生命本身一直存在着醫(yī)藥衛生的危機,由此造就的生命倫理(lǐ)觀念,也明顯離異于西方道德(dé)和宗教模式。其次,儒釋道文(wén)化、尤其是儒學(xué)與道學(xué),一直直接融潤和轄控着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的基本理(lǐ)論,以醫(yī)學(xué)哲學(xué)包括生命倫理(lǐ)思想或理(lǐ)論,是附屬和依附于儒釋道思想、精(jīng)神和語言;生命倫理(lǐ)觀念隻是鑲嵌于其中(zhōng)的一塊具(jù)有(yǒu)動感的寶石。當然,道術與易醫(yī)又(yòu)具(jù)有(yǒu)十分(fēn)獨特的哲學(xué)背景和生命倫理(lǐ)内核,如此,作(zuò)者也在書中(zhōng)有(yǒu)所關注。第三,鴉片戰争以後的中(zhōng)西文(wén)化大交合、大碰撞的潮汐高漲之後,特别是西方基督醫(yī)學(xué)的入駐,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逐漸被仄逼進一個有(yǒu)限的區(qū)域,而新(xīn)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已經被迫改變了原有(yǒu)的純淨的架構,服膺于西方化的科(kē)學(xué)規範和原則以及世界主義精(jīng)神的生命倫理(lǐ)學(xué),已經淹沒和遮蔽了中(zhōng)華民(mín)族獨有(yǒu)的醫(yī)學(xué)和生命倫理(lǐ)個性,其中(zhōng),不乏對于民(mín)族曆史積澱的精(jīng)華的鲸吞或遺棄,即使我們用(yòng)心挖掘、搶救與保護,但我們可(kě)以看到的确實嚴重扭曲與變形的經過粉飾的“遺産(chǎn)”。第四,中(zhōng)華民(mín)族的醫(yī)學(xué)并使漢民(mín)族一方的大中(zhōng)醫(yī)、大國(guó)醫(yī)概念,應該包括其他(tā)民(mín)族豐富的文(wén)化資源,有(yǒu)些具(jù)有(yǒu)十分(fēn)特殊的科(kē)學(xué)品質(zhì)和倫理(lǐ)特性;比如回族醫(yī)學(xué)道德(dé)的伊斯蘭文(wén)化因素;維吾爾醫(yī)學(xué)道德(dé)除伊斯蘭文(wén)化成分(fēn)外與中(zhōng)亞各民(mín)族之間的彙合;蒙藏醫(yī)學(xué)道德(dé)與佛教文(wén)化之間的内在聯系;其他(tā)如苗、羌、傣、壯、東巴等民(mín)族醫(yī)學(xué)道德(dé)各自獨有(yǒu)的倫理(lǐ)文(wén)化基因。第五,生命倫理(lǐ)學(xué)從經典階段向後現代的轉換,主要是自由意志(zhì)論世界主義向自由世界主義的精(jīng)神根基的進化,這個過程中(zhōng),表達了生命政治文(wén)化的變遷以及人類對于生命神聖意義的理(lǐ)解和對個體(tǐ)生命自主權利的尊重,人類始終沒有(yǒu)放棄通過醫(yī)學(xué)的善和愛的語言叙事對于健康的真全生活的追求,而在各自的醫(yī)學(xué)科(kē)學(xué)化的發展中(zhōng),以整全的生命倫理(lǐ)作(zuò)為(wèi)航标,創造新(xīn)的身體(tǐ)倫理(lǐ)的模式,使人類的福祉不緻于永遠(yuǎn)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夢境。生活是現實的,特别是對于病者和傷殘的人,對他(tā)們來說,恢複健康與解除痛苦不應該僅僅是一種祈盼,如是,我們的醫(yī)學(xué)、不管是西方醫(yī)學(xué)還是民(mín)族醫(yī)學(xué),在倫理(lǐ)上,應該做些什麽最重要的事、應該如何把醫(yī)學(xué)之愛付之于行動?

我們曾經在倫理(lǐ)學(xué)的诠釋中(zhōng),制造了很(hěn)多(duō)新(xīn)的概念,特别是作(zuò)為(wèi)有(yǒu)關生命科(kē)學(xué)技(jì )術與臨床醫(yī)學(xué)以及維護身體(tǐ)的康健的政策方面,我們投入了許多(duō)刻苦的熱情。為(wèi)人的身體(tǐ)的不幸而悲戚,為(wèi)人的生命的權利而疾呼和奮争,并在生命倫理(lǐ)的指向上,力圖用(yòng)他(tā)治的倫理(lǐ)責任替代自治的道德(dé)。道德(dé)理(lǐ)想之一是使個體(tǐ)生存自由成為(wèi)人類普遍的追求,并且從自在的意識中(zhōng),具(jù)體(tǐ)确立使自我的責任成為(wèi)為(wèi)他(tā)人謀取生命的權利。
中(zhōng)國(guó)儒家古訓,于醫(yī)道之術,蓋仁術喻指醫(yī)術。 “醫(yī)乃仁術”為(wèi)大醫(yī)精(jīng)誠所緻。《孟子·梁惠王上》雲:“無傷也,是乃仁術。”仁術也是愛之術,人道之術,也是精(jīng)益求精(jīng)之術。有(yǒu)利無傷害,是醫(yī)學(xué)倫理(lǐ)的國(guó)際通用(yòng)原則,以病人利益為(wèi)最高利益,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本精(jīng)神。仁術之目的是博愛的藝術,是至善之術;“至善”為(wèi)《大學(xué)》開篇的第一句話:“大學(xué)之道,在明明德(dé),在新(xīn)民(mín),在止于至善”。在《大學(xué)章句》中(zhōng),朱子将之稱為(wèi)《大學(xué)》的“三綱領”。無論明明德(dé)還是新(xīn)民(mín),都必須“止于至善”:仁術至善,即指我們醫(yī)務(wù)人員以精(jīng)到的醫(yī)術行天理(lǐ)、天道,以親民(mín),以善和愛這一醫(yī)學(xué)倫理(lǐ)之核心作(zuò)為(wèi)我們為(wèi)醫(yī)的“大道”。我們的醫(yī)道是人世間之大道,是替天行道,是人間正道,古人認為(wèi),醫(yī)道乃為(wèi)天德(dé),元·王好古《此事難知·序》中(zhōng)說:“蓋醫(yī)之為(wèi)道,所以續斯人之命,而與天地生生之德(dé)不可(kě)一朝泯也。”中(zhōng)華民(mín)族以“道”作(zuò)為(wèi)我們的信仰,道學(xué)、道統、道家深刻影響我們的醫(yī)家操守;孔子《禮記》告誡:大道之行,天下為(wèi)公(gōng)。興大道、行大道、循大道,即我們的醫(yī)之道,也即天之道。醫(yī)生的天職,是幫助延續人們的生命健康。這種道所體(tǐ)現出來的德(dé)和天地長(cháng)養萬物(wù)的大公(gōng)無私之德(dé)相一緻,它是佛性随緣而生利他(tā)妙用(yòng)的生生之德(dé)。作(zuò)為(wèi)醫(yī)生,一刻也不應缺少這種德(dé)。此“大道”集合了中(zhōng)華民(mín)族儒釋道傳統的内在精(jīng)華。同時,叙說了哲學(xué)家伊曼紐爾·康德(dé)的名(míng)言“頭上的星空,心中(zhōng)的道德(dé)律”,即“天”和“大道”。中(zhōng)國(guó)為(wèi)中(zhōng)央之國(guó),中(zhōng)華民(mín)族為(wèi)中(zhōng)道之民(mín)族,以“和”文(wén)化為(wèi)重要道德(dé)傳統,和氣生貴,和氣維道,家和萬事興。中(zhōng)和為(wèi)中(zhōng)庸之道,是中(zhōng)國(guó)文(wén)化的骨髓,作(zuò)為(wèi)一種方法論,它已經深深滲透到了與中(zhōng)國(guó)文(wén)化有(yǒu)關的每一個元素和成分(fēn)之中(zhōng),成為(wèi)構成普遍的文(wén)化心理(lǐ)和社會心理(lǐ)的核心要素之一。每個置身于中(zhōng)國(guó)文(wén)化視野中(zhōng)的社會成員,無論你願不願意,承不承認,你都無法擺脫那與生俱來的中(zhōng)庸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因此,在醫(yī)務(wù)活動中(zhōng),正确地認識中(zhōng)庸之道,并加以合理(lǐ)的應運,既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無可(kě)回避的文(wén)化責任。《尚書》的《盤庚篇》的“各設中(zhōng)于乃心”、《呂刑》“罔非在中(zhōng)”、《酒诰》的“作(zuò)稽中(zhōng)德(dé)”等。在《尚書·大禹谟》中(zhōng),有(yǒu)被宋儒稱為(wèi)“十六字心傳”的那一著名(míng)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jīng)惟一,允執厥中(zhōng)。”《尚書·洪範》記載,周武王向殷代的遺臣箕子請教國(guó)事,箕子提出九條大法,其中(zhōng)就有(yǒu)中(zhōng)道的思想:“無偏無頗,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由此,我們可(kě)以把《尚書》中(zhōng)強調“執中(zhōng)”的生命政治智慧,看作(zuò)是中(zhōng)庸之道的思想源頭。“中(zhōng)庸”一詞,語出《論語·雍也》。中(zhōng)和,作(zuò)為(wèi)生命倫理(lǐ)智慧,更契合于亞裏斯多(duō)德(dé)的過猶不及思想,得數有(yǒu)常,天地循常庸之道,是最美好的道。醫(yī)由此“道”,方有(yǒu)所得(德(dé)),乃“道德(dé)”是也。科(kē)學(xué)哲學(xué)從物(wù)理(lǐ)正負中(zhōng)和與化學(xué)中(zhōng)的“化合”獲得啓示,為(wèi)醫(yī)之道,必克服各種矛盾和痛苦,化解病理(lǐ)、心理(lǐ)和人理(lǐ)的沖突,恢複健康和平和,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中(zhōng)和更有(yǒu)寬容、寬厚、寬松、和諧、平和之意,在當下醫(yī)患關系緊張的情勢下,“中(zhōng)和”思想是十分(fēn)寶貴的,是我們繼承和發揚中(zhōng)華民(mín)族的道德(dé)哲學(xué)遺産(chǎn)。使我們的民(mín)生組織和機構成為(wèi)公(gōng)民(mín)信賴的和諧、溫馨、充滿親情的小(xiǎo)社會。
在對道德(dé)的解讀與诠釋上,我們這個民(mín)族做了太多(duō)的事,下了太多(duō)的功夫,給我們悠遠(yuǎn)的曆史,留下了不小(xiǎo)的财富,但也曾經餘存太多(duō)的遺憾與負面的影響。

中(zhōng)華民(mín)族的道德(dé)有(yǒu)其特有(yǒu)的民(mín)族性、本土性,而作(zuò)為(wèi)文(wén)化傳統,通過幾千年曆史的嬗變,其内涵已有(yǒu)很(hěn)大改變。在道德(dé)或所謂“倫理(lǐ)”的語義認知與理(lǐ)解上,中(zhōng)華民(mín)族一直沒有(yǒu)停止與外來民(mín)族或外來文(wén)化的交融或互為(wèi)影響,不能(néng)說,我們是一個完全的孤獨的、單一的道德(dé)教化的民(mín)族。
應該說,中(zhōng)西道德(dé)文(wén)化差異和情感上難以真正徹底互融,是客觀存在的。
其實,我們應該同意,亞裏士多(duō)德(dé)所言:德(dé)性是一種支配我們選擇的氣質(zhì)。這句話,其實他(tā)回避了對德(dé)性或道德(dé)本質(zhì)的概念诠釋,而隻是說明了道德(dé)的功能(néng),等于沒有(yǒu)言說什麽和如何判斷以及如何選擇才是道德(dé)的,或者那樣去做就是正當或善。結果,留下了一個結論,也就是道德(dé)之事是不言而喻的。
學(xué)人錢穆言:“言其德(dé)性,斯謂之誠矣。”他(tā)又(yòu)說,猶如莊老哲學(xué)的自然,道德(dé)須以誠為(wèi)貴,誠者實為(wèi)自成,是物(wù)之終始。中(zhōng)國(guó)古人認為(wèi),正德(dé)利用(yòng)厚生,在内正德(dé),方能(néng)在外有(yǒu)利用(yòng),最後以生命的安(ān)平、身體(tǐ)的康健為(wèi)目的。醫(yī)學(xué)更應以道德(dé)為(wèi)前提,敬畏生命為(wèi)最終的追求。這樣的生命倫理(lǐ)觀念,為(wèi)道德(dé)的诠釋提供了一個明晰的基礎。持有(yǒu)正道,方具(jù)德(dé)性,循正道尊德(dé)性才可(kě)德(dé)(得)行。
米蘭·昆德(dé)拉的小(xiǎo)說《生活在别處》的前言中(zhōng),一再對我們說,要反對既定的思維模式,絕不墨守成規和媚俗取寵,要用(yòng)一種新(xīn)的美感與道德(dé)觀,解答(dá)“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麽”,他(tā)用(yòng)瑪曼重複艾呂雅的詩句來回應人類對于身體(tǐ)道德(dé)的疑問和困惑。
“一隻眼睛裏有(yǒu)月亮,一隻眼睛裏有(yǒu)太陽。”
昆德(dé)拉通過筆(bǐ)下人物(wù)的語言,道出不能(néng)言說的倫理(lǐ)和宗教的律令,并對于傳統的“善”的觀念所謂不言而喻以緻被濫用(yòng)的文(wén)化社會,進行批評,羅伯特·施佩曼無情地拆解醫(yī)生的職業道德(dé)觀念:
他(tā)們隻是對于健康的風險進行消極地說明,緩和地規勸說:“倘若健康對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對您是最好的。”用(yòng)對一位患有(yǒu)肺炎的患者(具(jù)有(yǒu)社會身份的人)勸說,不要做出違反身體(tǐ)健康或疾病治療的行為(wèi),那樣的“惡”是醫(yī)療的倫理(lǐ)規則不能(néng)容忍的。
施佩曼說明了醫(yī)生有(yǒu)責任對病人傳達為(wèi)了保全生命必須摘除腎髒或者截肢的治療為(wèi)什麽是合理(lǐ)的,也進一步追求,應該為(wèi)此專門為(wèi)此類行為(wèi)的責任規範,建立一門倫理(lǐ)學(xué)。當然,這些都源于人類的道德(dé)傳統和對于幸福的理(l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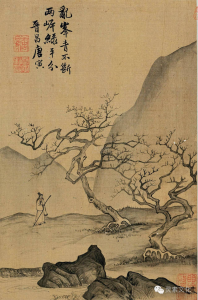
倫理(lǐ)學(xué)作(zuò)為(wèi)一門學(xué)科(kē),出于“宇宙萬物(wù)都是向善的。一切技(jì )術和科(kē)學(xué)都有(yǒu)目的。”對于善、幸福與責任,應該有(yǒu)一門學(xué)科(kē),去研究,為(wèi)生活做顧問,特别是技(jì )術與科(kē)學(xué)行為(wèi)。選擇與判斷,需要理(lǐ)由和依據。對于善與惡的評價,要有(yǒu)标準和理(lǐ)由;對财富的分(fēn)配,要有(yǒu)原則,說服那些沒有(yǒu)獲得所求利益的人;關于公(gōng)正和權利,我們要解決有(yǒu)此類事件所引發的沖突,等等;因此,我們要制造一門倫理(lǐ)學(xué)。
身體(tǐ)倫理(lǐ)學(xué)可(kě)以作(zuò)為(wèi)生命倫理(lǐ)學(xué)的變體(tǐ),以此回應文(wén)化意義和生物(wù)學(xué)意義的人的生命存在和社會空間權利或人與人關系的諸多(duō)可(kě)能(néng)性,也可(kě)更直接地表達人的身體(tǐ)價值和道德(dé)效益。同樣,生命倫理(lǐ)學(xué)也可(kě)以作(zuò)為(wèi)身體(tǐ)倫理(lǐ)實現它的學(xué)術追問和學(xué)科(kē)理(lǐ)念。凡是關于人的肉身與精(jīng)神的道德(dé)問題的研究,可(kě)以構成身體(tǐ)倫理(lǐ)學(xué)的全部内容,身體(tǐ)倫理(lǐ)更直接與具(jù)象地對人的生死疾病、苦難、欲望、快感進行倫理(lǐ)的辨析與對話,并把肉身的真實體(tǐ)驗和他(tā)者的測查、道德(dé)認知、觀念以及主體(tǐ)表達,進行綜合地審視或評價,最後獲得權利等級的排序,以求得問題或案例解決的方案和計算。身體(tǐ)倫理(lǐ)學(xué)較之生命倫理(lǐ)評價更為(wèi)精(jīng)緻與細膩,它并不排斥精(jīng)神與靈性的偵查、覺悟與沉思,而更突出和強化了身體(tǐ)的社會性和生命政治意義,更符合物(wù)質(zhì)的實存所引發的衛生經濟價值與身體(tǐ)的文(wén)化功效。在此,隻要有(yǒu)倫理(lǐ)的要素始終參與對于人性的反省,就不至于将身體(tǐ)物(wù)化或僅僅是作(zuò)為(wèi)失人性的符号。如此,人的身體(tǐ)會更加自由,更有(yǒu)尊嚴,更加個我化。人類倫理(lǐ)研究,更貼近于現實生活,會加強醫(yī)學(xué)或生命科(kē)學(xué)技(jì )術的親切感,更會顯現個人世界主義意識,提高醫(yī)生與病人交流的質(zhì)量和效率。
我們身體(tǐ)的文(wén)化與社會意義,在于它承擔思想和情感的實現功能(néng),由此,才可(kě)以通過這種身體(tǐ)的叙事,來表示善或者惡的訴求,以其達到道德(dé)理(lǐ)想,使無數個體(tǐ)建立各種關系,并接受權利和權力,拒絕暴力的鞭打和壓迫。身體(tǐ)是實現生命倫理(lǐ)意向的唯一工(gōng)具(jù),因此,身體(tǐ)的概念絕非僅僅限于物(wù)質(zhì)的平面,而其廣度與深度都與心理(lǐ)、精(jīng)神、靈性的功能(néng)緊密相連,有(yǒu)時合為(wèi)一體(tǐ),身體(tǐ)可(kě)以替代(幾乎是一種常态)思想和意志(zhì),實現人的活動和創造力,旨在于完成“心”的召喚和命令,但如果沒有(yǒu)身體(tǐ)的同一或同步配合,道德(dé)效應隻能(néng)等于空靈。醫(yī)學(xué)生活和疾病過程是一個社會和技(jì )術的肉身反應和身體(tǐ)的病理(lǐ)性經驗,沒有(yǒu)它,人的身體(tǐ)也就沒有(yǒu)展開的空間和施治、愛的對象。隻有(yǒu)醫(yī)學(xué)生活有(yǒu)效的恢複到健康的正常的程序化生活,身體(tǐ)才能(néng)找到自身的完整性:主體(tǐ)的生命社會化秩序才可(kě)以建立,與之相關的人的活動才可(kě)以展開和運行,才能(néng)夠使倫理(lǐ)性和生理(lǐ)性獲得完美結合。所以,梅洛·龐蒂說,身體(tǐ)“本質(zhì)上是一個表達空間”,因此,“身體(tǐ)的空間性……是一個有(yǒu)意義的世界形成的條件。”并斷言“身體(tǐ)是我們能(néng)擁有(yǒu)世界的總的媒介”。而美國(guó)社會學(xué)家約翰·奧尼爾則在《身體(tǐ)形态》一書中(zhōng)更詳盡地指出:身體(tǐ)是我們賴以栖居的大社會和小(xiǎo)社會所共有(yǒu)的美好工(gōng)具(jù)。身體(tǐ)同樣是我們在社交中(zhōng)表達親昵和熱情的工(gōng)具(jù)。

人的行為(wèi)或生活行動的法則主要接受倫理(lǐ)觀念的控制,比如公(gōng)正和愛;這是由理(lǐ)性對整體(tǐ)秩序的約束所支配。理(lǐ)性在倫理(lǐ)上由理(lǐ)論思想構成,在觀念上與可(kě)理(lǐ)解性上是由倫理(lǐ)本身構成。胡塞爾的理(lǐ)性強調存在的重要性,它覆蓋了“整個人類存在的意義和無意義的各種問題”。作(zuò)為(wèi)身體(tǐ)現象學(xué)來說,對于“我”與“他(tā)者”共現在一種完全的心理(lǐ)和身體(tǐ)的“共存”唯我論經驗之中(zhōng),是通過觸感和情感統一在心理(lǐ)場和感覺場之中(zhōng),隻有(yǒu)在其心理(lǐ)和身體(tǐ)進行聯系時,主體(tǐ)才會有(yǒu)意識把身體(tǐ)作(zuò)為(wèi)自我的一個替代。笛卡爾的神聖真實性是建立在生命的那個特指的身體(tǐ)觀念自明性的基礎上,胡塞爾則從現象出發,分(fēn)析本質(zhì)中(zhōng)居有(yǒu)一個“他(tā)我”的身體(tǐ)觀念,即把身體(tǐ)的自然和理(lǐ)性意向分(fēn)開,制造了一個“自我”和“他(tā)我”的相異性。這樣我們就可(kě)以将身體(tǐ)分(fēn)别以醫(yī)學(xué)、物(wù)理(lǐ)學(xué)、哲學(xué)、宗教或藝術、社會學(xué)視角做出不同的評價,而最後用(yòng)倫理(lǐ)學(xué)的最高本體(tǐ)收集與整理(lǐ),獲得整全的生命倫理(lǐ)形式,歸結為(wèi)人的醫(yī)療行為(wèi)的正當性選擇,而就不至于被身體(tǐ)的擴延的意念知覺和痛苦或快感的經驗所困惑。
人的身體(tǐ)有(yǒu)時被分(fēn)離,但這種分(fēn)離的整體(tǐ),依然作(zuò)為(wèi)身體(tǐ)本身,人通過身體(tǐ)移動進行感知,表達自己的存在,我們的肉體(tǐ)“充當在次級還原中(zhōng)不再形成客觀世界而是極其重要的自然、固有(yǒu)的自然的所有(yǒu)身體(tǐ)的參考極。”因此,胡塞爾進一步分(fēn)析道:
“由于這種對一切陌生事物(wù)的抽象消除,為(wèi)我們保留的是一種世界,一種被還原為(wèi)固有(yǒu)的本性,正是因為(wèi)肉身,即心理(lǐ)-勝利的自我、肉體(tǐ)、靈魂和個體(tǐ)的自我,還原世界獨一無二的特點才融入到本性當中(zhōng)。”
人的自我的自身和自然的自身之抽象遠(yuǎn)遠(yuǎn)超過由教育習成的虛構形式或想象,我們日常對身體(tǐ)的理(lǐ)解僅僅是一種化身,自己的自然是以我為(wèi)中(zhōng)心的自然,是可(kě)以運用(yòng)權力的境遇,它是可(kě)以看到、聽到、觸摸到的;身體(tǐ)作(zuò)為(wèi)物(wù)質(zhì)的肉身是這種對本有(yǒu)境遇的還原,至此,身體(tǐ)依然是沒有(yǒu)被察覺的器官,依然沒有(yǒu)被“我”的行為(wèi)滲透的器官,“我”的行為(wèi)最終以事物(wù)終止,這就是我和我的肉身。問題是,我們必須有(yǒu)一個确認自身是“我”的過程,如何獲得在場的自身成為(wèi)他(tā)者的在“這裏”的體(tǐ)驗,我可(kě)以自由地駕馭和控制我的身體(tǐ),并使得我的身體(tǐ)透視的原點所接受的經驗體(tǐ)系的方向和他(tā)這另外的經驗體(tǐ)系的方向的統一,使身體(tǐ)的雙重歸屬合法地被不同的視覺評價後實現最後的同步,由此避免他(tā)者逃逸“這裏的我”,背叛自身原我的道德(dé)意義。人類的身體(tǐ)應該最終結束和圓滿完成局部孤立的平行活動(愉快),另外就是完善亞裏士多(duō)德(dé)所稱道的工(gōng)具(jù)的功能(néng)(人類的成果);此外,達到康德(dé)稱道的決心實現的人類重點,即命運或計劃,也就是我們所描述的幸福。幸福不是欲望的全部,身體(tǐ)内不可(kě)能(néng)絕對自由,人隻是一種通過身體(tǐ)的承諾,隻能(néng)享有(yǒu)有(yǒu)限的欲望滿足快樂因為(wèi)時間的限制,隻是局限的完美。生命的進程是由人的身體(tǐ)指定和呈現,我們的身體(tǐ)無法逃脫自然所規範的倫理(lǐ)程式,即使我們經常充盈着身體(tǐ)表達的自由意志(zhì)的沖動與激情,我們也不能(néng)放任它和“自我”的解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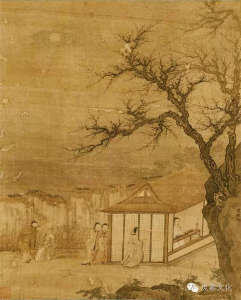
對身體(tǐ)形象的體(tǐ)驗、感覺、記憶以及聯想、想象,對于身體(tǐ)患病中(zhōng)疼痛的放大、誇張、外顯圖示的延伸、編織、杜撰和猜想,皆建立在原始的身體(tǐ)空間性外殼以及肉性基質(zhì)的描述與語言中(zhōng)。醫(yī)生用(yòng)科(kē)學(xué)和技(jì )術的“看”來拷問疾病的元素和因果關系,用(yòng)己身的知覺,分(fēn)析他(tā)者呈示或給予的非正常身體(tǐ)現象,以求得疾病的診斷,獲得治療的意見。醫(yī)生以個人的身體(tǐ)去接觸病人的身體(tǐ),形成身體(tǐ)與身體(tǐ)的相互交通,成為(wèi)被關注、被愛護、被救治的主體(tǐ),接受另外一個職業的施愛與權力的主體(tǐ)的道德(dé)行動目的和倫理(lǐ)追求。生命倫理(lǐ)學(xué)則更加生動和具(jù)象、外顯、現實以及易于體(tǐ)驗與理(lǐ)解。
“道,可(kě)道,非常道;名(míng),可(kě)名(míng),非常名(míng)。無,名(míng)天地之始;有(yǒu),名(míng)萬物(wù)之母。”
道為(wèi)宇宙本體(tǐ),道為(wèi)萬物(wù)之源,道為(wèi)事物(wù)變化運行的規律。《道德(dé)經》與猶太-基督教的《舊約:創世紀》相互呼應:“太初有(yǒu)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wù)是藉着他(tā)造的:凡被造的,沒有(yǒu)一樣不是藉着他(tā)造的。生命在他(tā)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這光就是世人的道,亦為(wèi)道法,唯有(yǒu)信他(tā)的,才可(kě)有(yǒu)道、得道,并方能(néng)培育愛養萬物(wù)之恩德(dé)。《聖經》開篇即道: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道是自在者(I am),“耶和華”(Yhwh-jehovah)、(夷、希、微)等,都是基督教的命理(lǐ),我是我所是的,即是:道是永在的造化者、超越者、富有(yǒu)的生命者、啓示者、公(gōng)益者與拯救者。在老子那裏獲得了全面的诠釋。并以生命的道理(lǐ),說明宇宙的大道。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老子之道,以自然為(wèi)來源;以無為(wèi)體(tǐ),以有(yǒu)為(wèi)用(yòng);以反始守柔為(wèi)處世之方。其言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yòng);天下萬物(wù)生于有(yǒu);有(yǒu)生于無。”
聞道幽昧深遠(yuǎn)之“道”,可(kě)會意、隻能(néng)會意其中(zhōng)蘊涵生命倫理(lǐ)之正道。
漢語言之“道”,既為(wèi)實又(yòu)為(wèi)虛,既為(wèi)有(yǒu)又(yòu)為(wèi)無;真理(lǐ)、規律與方略,皆為(wèi)道。道為(wèi)生命之來源,如《系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zuò)成物(wù)。”乾坤二卦表述了中(zhōng)國(guó)古代醫(yī)學(xué)的基礎和宇宙之物(wù)力取向,乾卦代表了大道的本體(tǐ)。人命歸于天,乃謂明道與命道。南懷瑾借易經的道說,解釋疾病和病理(lǐ)生理(lǐ),同時關注易學(xué)的醫(yī)學(xué)倫理(lǐ)之道,透悟出生命的倫理(lǐ)之學(xué),可(kě)謂機巧。
因為(wèi)人類要攫取“道之用(yòng)”來規範行為(wèi),引導善行,則以求道義,縮微精(jīng)到之,可(kě)謂“義之道”、正義之道。義指一種立法、衛法、守法的行動和規則,是政治、社會的根本原理(lǐ),也是道德(dé)的根本原理(lǐ)。郭沫若考證,“德(dé)”中(zhōng)有(yǒu)正直、正義的道德(dé)觀念,中(zhōng)華民(mín)族從周代開始,把“義”作(zuò)為(wèi)百德(dé)之王。
“禮以行義”,“德(dé)義,利之本也。”這是中(zhōng)華文(wén)化的義德(dé)的遺産(chǎn)。與此相對照,西方的道德(dé)觀念與生命政治觀念,格外強調政治與法。
“古今中(zhōng)外,并不是先有(yǒu)禮與法,而後有(yǒu)道德(dé)上的“義”或“義道”,實際上是先有(yǒu)人民(mín)或社會公(gōng)認的道義,而後有(yǒu)一定的禮法或法典(……是人民(mín)要求的正義與道德(dé)規範)。”
先于華夏文(wén)化的尼羅河文(wén)化中(zhōng),即公(gōng)元前21世紀,和古希臘宙斯的女兒Dike主管“義”一樣,人們崇拜的諸神中(zhōng)有(yǒu)一位Maat女神,其職責即是義、正、中(zhōng)、平,她是農神Osiris的女兒,手握天枰,西人把Maat譯為(wèi)主管公(gōng)正、真理(lǐ)和公(gōng)義之神。公(gōng)元前2000年,埃及的一位明君普塔豪特普(Ptahotep)的墓志(zhì)銘就是:“公(gōng)正或義,勝過所有(yǒu)。”雅利安(ān)人征服後的古代印度,混融了“義德(dé)”文(wén)化,創造了達摩(Dharma)一詞,與Maat一樣,示表“義”的主德(dé)。釋迦摩尼用(yòng)“去惡行慈”普救百姓脫離困苦,把韋陀和婆羅門的那種強硬的達摩義法(伐),改造為(wèi)慈悲的義道和義術。
基督教聖經從摩西五經開始,一直到《啓示錄》,不管是《舊約》還是《新(xīn)約》,都是叙事一個“義”字,是巴比倫文(wén)化、希伯來文(wén)化、古代埃及文(wén)化以及古希臘等文(wén)明的混合積澱和結晶。聖經的義德(dé)文(wén)化細膩而精(jīng)緻,如“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如不勝于文(wén)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néng)進天國(guó)。”通過神的話語,說明“義”的含義的差異。路德(dé)的因“信”道而成“義”道,便為(wèi)人類的正義之道開了先河。
但是正義(justice)或公(gōng)正(righteousness)在基督教文(wén)化中(zhōng),以至于對于世俗社會道義德(dé)性的影響、使用(yòng)與延伸中(zhōng),又(yòu)十分(fēn)複雜與寬泛。對于基督徒來說,其正義就是對于上帝傑明的恪守與遵循,對于上帝來說,正義就是正直的楷模形象以及對于人的德(dé)性的引導與教誨,并在具(jù)體(tǐ)分(fēn)配利益時給以公(gōng)平的評價與裁判,即重新(xīn)分(fēn)配權利(retribution)。耶稣在“山(shān)中(zhōng)寶訓”中(zhōng)為(wèi)門徒描述的正義,主要是道德(dé)的,而不是遵守法律或形式主義外化的“義”,完全是人的一種自覺的善的品質(zh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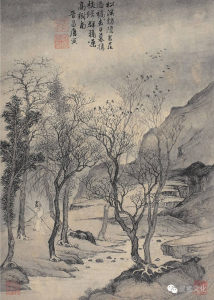
西方的義,主要追求公(gōng)平之正義,平等觀念中(zhōng)的義,除一神一主外,人皆兄弟(dì),中(zhōng)國(guó)人為(wèi)差等的義,主張親親、君君、臣臣的等級義序;西方人是由上帝或神祗作(zuò)為(wèi)義德(dé)的引導者和義人的主宰,中(zhōng)國(guó)人往往以帝王或聖旨代表天命之大義;西方依律法監督不義之行,維持義德(dé)秩序,中(zhōng)國(guó)人以伐(罰)和禮義、仁義為(wèi)重;西方人以信望愛來維系義德(dé),中(zhōng)國(guó)人以文(wén)治武功、交相利、智仁勇維系義之道。以上為(wèi)中(zhōng)西義德(dé)文(wén)化的差異。
醫(yī)學(xué)的正義也是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規範,是指導人在醫(yī)療過程中(zhōng)的行為(wèi)原則;醫(yī)學(xué)正義是一種評價标準,核查與決定是否接受某一行為(wèi)的憑據;醫(yī)學(xué)正義佐證了人的行動的義務(wù)性與合法性。因為(wèi)這一正義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時符合社會利益與自然規律,因此,醫(yī)學(xué)的正義必須滿足人的權利的需要;這一原則含有(yǒu)強制、明确并對被損害的利益的必要補償的特征。對于義務(wù)論所指的醫(yī)學(xué)正義而言,其形式可(kě)分(fēn)為(wèi)互相交換與互惠、衛生資源和生命權利分(fēn)配的合理(lǐ)性、服從普遍的社會利益需要、平衡與均平各社會成員之間的正義、愛、自由的權利。
羅爾斯的正義倫理(lǐ)試圖以社會正義的規範倫理(lǐ)學(xué)替代古典功利主義和康德(dé)的義務(wù)論倫理(lǐ)學(xué),試圖為(wèi)社會制度的公(gōng)正安(ān)排提供理(lǐ)論依據。羅爾斯把正義稱之為(wèi)“公(gōng)平的正義”。正義原則是用(yòng)來分(fēn)配公(gōng)民(mín)的基本權利和義務(wù),劃分(fēn)由社會合作(zuò)産(chǎn)生的利益和負擔的主要政治和經濟制度。在羅爾斯看來,人們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體(tǐ)制和一般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也受到人們出生伊始就具(jù)有(yǒu)的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自然秉賦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而且這種不平等又(yòu)是個人無法自由選擇的,這種不平等就是正義原則的最初應用(yòng)對象。換言之,即正義原則就是要通過社會制度的合理(lǐ)正當調節,來從全社會角度處理(lǐ)這種出發點方面的不平等,盡量排除社會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對于人們生活前景和經濟狀态的影響。
羅爾斯的“作(zuò)為(wèi)公(gōng)平的正義”理(lǐ)論體(tǐ)現的是一種經濟倫理(lǐ)思想,體(tǐ)現一種生命原則、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對于衛生資源的合理(lǐ)優化配置提供了某些理(lǐ)論依據。在衛生資源有(yǒu)限的境況下,如何解決衛生資源的來源和使用(yòng)問題,要在同時照顧公(gōng)共、公(gōng)衆利益又(yòu)要做到每個人享有(yǒu)極大的公(gōng)正和生命平等,是個難度很(hěn)大的衛生經濟倫理(lǐ)學(xué)問題,在這裏蘊藏着進行衛生經濟決策和改革、規範衛生行為(wèi)的理(lǐ)論依據和重要原則。因此,公(gōng)正的理(lǐ)想擴大并強化了個人和政府的責任。如果說正義論是從社會制度的倫理(lǐ)精(jīng)神進入醫(yī)學(xué)倫理(lǐ)和生命倫理(lǐ)視域并為(wèi)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體(tǐ)系建構提供了一個理(lǐ)論視域和建構路徑,那麽,“義務(wù)論”主要是從個體(tǐ)行為(wèi)的規範性切入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和生命倫理(lǐ)學(xué)的。
傳統的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是以義務(wù)論為(wèi)軸心的體(tǐ)系。圍繞道德(dé)義務(wù)的根本信念而建立起來的對醫(yī)學(xué)主體(tǐ)的各種美德(dé)要求與美德(dé)規勸,體(tǐ)現道德(dé)義務(wù)與美德(dé)的各種規範與應盡的責任要求等等,都是傳統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的重要内容。在當代生物(wù)醫(yī)學(xué)的發展帶來的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轉型的過程中(zhōng),不能(néng)夠否認義務(wù)論在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發展中(zhōng)和醫(yī)德(dé)實踐中(zhōng)曆史作(zuò)用(yòng)和重要地位,甚至可(kě)以認為(wèi)義務(wù)和美德(dé)是醫(yī)學(xué)行為(wèi)的道德(dé)底線(xiàn)。隻是要充分(fēn)地認識到,科(kē)學(xué)和技(jì )術的發展帶來的一系列道德(dé)難題和醫(yī)學(xué)道德(dé)的時代性困境,僅僅以義務(wù)論作(zuò)為(wèi)理(lǐ)論基礎和方法手段是十分(fēn)單調、軟弱和殘缺的。從現代哲學(xué)和倫理(lǐ)學(xué)理(lǐ)論中(zhōng)吸收必要的營養、從當代生物(wù)醫(yī)學(xué)的發展實際情況出發創新(xīn)醫(yī)學(xué)倫理(lǐ)理(lǐ)論是當代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的曆史使命和當務(wù)之急。事實上,當代生命倫理(lǐ)學(xué)的發展就是理(lǐ)論創新(xīn)和實踐創新(xīn)的結果。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由義務(wù)論規導醫(yī)學(xué)行為(wèi)的道德(dé)方向,到生命倫理(lǐ)學(xué)由義務(wù)論、公(gōng)益論和價值論引領現代生物(wù)醫(yī)學(xué)的發展走出道德(dé)困境,表明義務(wù)論既不能(néng)退出曆史舞台,也不能(néng)繼續獨自擔當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發展的重任。現代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的發展需要解決具(jù)體(tǐ)醫(yī)學(xué)道德(dé)問題,同時更需要建立與之相适應的新(xīn)的理(lǐ)性思維,否則,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的發展就可(kě)能(néng)缺乏理(lǐ)性支撐和缺少終極思考,割裂倫理(lǐ)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絕對性與相對性的辯證關系。
事實上,醫(yī)學(xué)倫理(lǐ)的規範生态應該是功利論與道義論的結合。如,無論是對現代生命科(kē)學(xué)技(jì )術、生命質(zhì)量和價值的判斷、死亡方式的選擇,還是醫(yī)療衛生改革與決策等,都必須在功利論和道義論的結合中(zhōng)才能(néng)得到合理(lǐ)性與合法性論證。現代高新(xīn)生命科(kē)學(xué)技(jì )術的迅速發展是醫(yī)學(xué)倫理(lǐ)學(xué)向生命倫理(lǐ)學(xué)發展的背景條件之一,這種轉變同樣根本無法回避功利論和道義論這兩種道德(dé)評價系統,無法回避存在于後現代醫(yī)學(xué)實踐中(zhōng)的種種“價值困境”以及在“道德(dé)價值”問題上的内在緊張及其與傳統倫理(lǐ)的某種斷裂,也不可(kě)能(néng)在個體(tǐ)生命和社會制度的二元分(fēn)裂中(zhōng)完成人文(wén)精(jīng)神和生命倫理(lǐ)精(jīng)神的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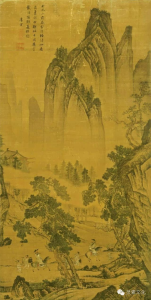
我依然以為(wèi),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包括少數民(mín)族的大家庭的醫(yī)學(xué)道德(dé)文(wén)化資源是極其寶貴并十分(fēn)豐富,值得我們去挖掘、醇化與清理(lǐ);但是,關于中(zhōng)醫(yī)學(xué),還應定位于一門非正規科(kē)學(xué),它具(jù)有(yǒu)馬塞爾·莫斯式的複雜性與文(wén)化的原始性,但具(jù)有(yǒu)特殊的科(kē)學(xué)精(jīng)神,已經剔除了初級性;由于它的特定的人種醫(yī)學(xué)的研究範圍,反映了黃河與長(cháng)江流域的肉體(tǐ)象征人類學(xué)和被沙漠相隔裂的形而上學(xué)與靈學(xué)概念鎖鏈,與儒道釋文(wén)化融彙,演變為(wèi)知識的、經驗的、工(gōng)具(jù)化的、感悟的、現象學(xué)的群體(tǐ)健康依賴與精(jīng)神、社會信仰;我們不能(néng)用(yòng)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的美索不達米亞區(qū)域的閃民(mín)族的兩河觀念,或地中(zhōng)海文(wén)化圈的西方科(kē)學(xué)觀框定、評價、審視、質(zhì)疑中(zhōng)醫(yī),西方主義的話語系統不适宜于對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和技(jì )藝的理(lǐ)解;隻有(yǒu)用(yòng)理(lǐ)性與非理(lǐ)性兩種方式,才能(néng)共同保存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結構的持續性,不要用(yòng)西方式的現代性符号霸權剝奪民(mín)族傳統和文(wén)化遺産(chǎn),隻能(néng)通過曆史的反思和反省,在泛文(wén)化和時空的跨越中(zhōng)融會在人類的精(jīng)神文(wén)化相關體(tǐ)中(zhōng),中(zhōng)醫(yī)的發展決定于人類的文(wén)化自覺,沒有(yǒu)必要借助于任何權力或暴力。應該說,醫(yī)學(xué)的誕生是目的化的,但不同文(wén)化思維和語言境遇,使各民(mín)族醫(yī)學(xué)不可(kě)類比,西方醫(yī)學(xué)的主體(tǐ)地位決定于其強大的效用(yòng)性、可(kě)驗證性、重複性、觀測性和體(tǐ)系化;但中(zhōng)醫(yī)應該有(yǒu)自己的品格和精(jīng)神,中(zhōng)醫(yī)應該自信;關于中(zhōng)醫(yī)的讨論隻是科(kē)學(xué)與非科(kē)學(xué)之争,不應作(zuò)為(wèi)科(kē)學(xué)與不科(kē)學(xué)或僞科(kē)學(xué)之争。中(zhōng)醫(yī)與西醫(yī)不是結合問題,而是與其他(tā)民(mín)族醫(yī)學(xué)長(cháng)期互補、共存;中(zhōng)醫(yī)的發展,首先是一種文(wén)化的變革,是一種中(zhōng)華民(mín)族獨有(yǒu)的思維與傳統的不可(kě)再生的經典載體(tǐ),其次才考慮一種生存工(gōng)具(jù)和生活方式的遷移與選擇習俗的變更。當代,中(zhōng)醫(yī)存在的最大危機是人文(wén)化和人文(wén)精(jīng)神的危機,是中(zhōng)醫(yī)管理(lǐ)隊伍、中(zhōng)醫(yī)醫(yī)務(wù)人員、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工(gōng)作(zuò)者和學(xué)者的責任感的淡化,導緻中(zhōng)醫(yī)學(xué)醫(yī)學(xué)科(kē)學(xué)目标和學(xué)科(kē)目的的迷失;中(zhōng)醫(yī)行政體(tǐ)制和權力的濫用(yòng)與腐敗,加重了這種方向感的錯位以及角色的失準。中(zhōng)醫(yī)的文(wén)化哲學(xué)讨論,應該以正面交鋒與争鳴為(wèi)主要形式,應該鼓勵組建中(zhōng)醫(yī)哲學(xué)内部和非中(zhōng)醫(yī)哲學(xué)的外部的學(xué)派,進行與語言或話語符号體(tǐ)系、意識、世界科(kē)學(xué)印記觀念以及宗教哲學(xué)方向的對話;同時考略與社會生活、道德(dé)習俗、政治體(tǐ)制、市民(mín)健康保健心理(lǐ)、經濟消費與傳媒價值、教育等關系。應該努力挖掘、激活和開發中(zhōng)華民(mín)族的醫(yī)學(xué)中(zhōng)特有(yǒu)的人文(wén)資源,并與西方的文(wén)化産(chǎn)品活思想進行比較性研究,這是一項十分(fēn)艱巨的使命。我們今天面對的這部關于中(zhōng)華生命倫理(lǐ)文(wén)化的作(zuò)品,就是試圖踐行這一動議指向的作(zuò)品,這是一個很(hěn)好的開端。
此時,我在茲有(yǒu)想,讀罷馬家忠君的這部書稿,深為(wèi)其努力和有(yǒu)心所撼動。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選題,也是一種嘗試和知性的冒險,因為(wèi)還沒有(yǒu)人系統地真正地用(yòng)大篇幅的學(xué)術文(wén)字去深入叙事如此這般的中(zhōng)華多(duō)民(mín)族醫(yī)學(xué)道德(dé)問題,并作(zuò)出學(xué)理(lǐ)評價與精(jīng)論。書中(zhōng)不乏精(jīng)彩的議論和前衛的思維。很(hěn)多(duō)是作(zuò)者多(duō)年的思想積澱和文(wén)化守望的成就。本書獨有(yǒu)的見地和智性的研究,顯然添補了這個領域研究中(zhōng)的空白,有(yǒu)很(hěn)多(duō)光耀閃爍的文(wén)字和頗有(yǒu)見地的意見,值得我們了悟和玩味,同時也啓發了我們後來的青年學(xué)人,如何規劃我們關注的項目和選題,如何避開把生命倫理(lǐ)學(xué)研究作(zuò)為(wèi)一種追随西方那種新(xīn)聞追蹤似的獵取,或者鹦鹉學(xué)舌似的作(zuò)秀;而應如何堅持民(mín)族的品性和中(zhōng)國(guó)的特性。當然,本書隻是這個議題的開始,很(hěn)多(duō)思考還限于一個開端,有(yǒu)些論述還不甚透徹和深刻,書中(zhōng)有(yǒu)些分(fēn)析還限于平面的話語,有(yǒu)些觀點也值得商(shāng)榷。當然,如何挖掘中(zhōng)華醫(yī)學(xué)遺産(chǎn)中(zhōng)的生命倫理(lǐ)學(xué)資源,不是一朝一夕的行動,這使我想到很(hěn)多(duō)學(xué)者緻力于儒家生命倫理(lǐ)學(xué)、道家生命倫理(lǐ)學(xué)或佛家生命倫理(lǐ)學(xué)的研究,已經有(yǒu)了很(hěn)可(kě)以環顧和凝視的成果,隻是還在一個過程之中(zhōng)的探索,無疑更有(yǒu)深層的測度和考量,想來,留給與本書作(zuò)者這個議題一并彙合起來,聚成一派中(zhōng)華生命倫理(lǐ)的大河,以其生命政治思想和中(zhōng)華生命倫理(lǐ)精(jīng)神的小(xiǎo)島,帶動和激蕩其生命倫理(lǐ)的自由世界主義的大海汪洋。
我念,本書作(zuò)者有(yǒu)更驚人的成果,在不久,奉獻給我們。
(作(zuò)者系東南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中(zhōng)醫(yī)藥大學(xué)中(zhōng)醫(yī)文(wén)化研究中(zhōng)心特邀研究員。)